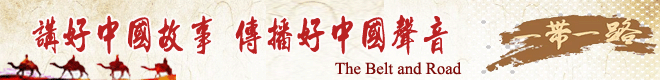
古城女杰传奇——记母亲程秀英
古城女杰传奇——记母亲程秀英
作者:郑渝辉
新中国成立初期,据当时母亲家乡人民政府调查统计,母亲是方圆千里,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唯一女性。
旧社会,妇女受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母亲有着早期革命思想的萌芽,与她童年、青年时期的遭遇分不开的。
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腐败的清朝政府不予抵抗,第二年签定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和封建社会。
然而,中国人民一直都未停止反抗,虽然最终在中外反动势力联合绞杀下失败,但是中国人民所表现的爱国气节为后人所传颂。
封建主义的统治集团为了维护摇摇欲坠的政权,其中大批有识之士,提出变法自救的主张,一心想改变国是贫弱的局面。这些措施虽然没有触及根本政治制度的变革,但都利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近代资产阶级进步思想文化的传播。
中国几千年封建帝制格局随着外来侵略一次次被撕裂,弱肉强食是不变的丛林法则。反侵略、反压迫,求新求变,大量先进的西方文化涌入中国。在北京、上海、南京、无锡、武汉、重庆等大城市建立了领使馆、办事处、办女校、西医院、传经布道、妇女放裹足等先进生活方式。
母亲就是出身在受近代史影响的时代大背景中。她的籍贯是:江苏省盰眙县古城镇。但出身地却在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江南鱼米之乡——无锡。

她是幸运的、又是不幸的。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五日还距出生前二十多天,亲生父亲程道铭就被一种叫:巴骨瘤痰(骨癌)的病夺去了年轻的生命。她作为遗腹女在母亲的腹中,来到无锡,在大姨妈的安排下,降生在这块土地上。
她的奶奶家是古城的富裕人家。十分封建,儿子的早逝怪罪母女俩为不祥之物,听说生了一个女儿后,更是嫌弃。
母亲出生后,姥姥为她取名“明圆”,意寓为:掌上明珠,一定要团圆。
她生命中第一个贵人就是大姨妈,名叫徐美,长得标致,身姿妙曼,双目传情,略通文墨,小鸟依人,又名“许美人”。经人介绍被上海驻法大使馆官员陈某某纳为姨太太。常驻上海过着那个时代妇女望尘莫及、锦衣玉食、风光无限的日子。
小明圆一天天长大,出落成人见人爱的小姑娘。
一次,大姨妈许美把明圆母女俩接到上海小住,大上海宽大的柏油马路、高楼大厦、车水马龙、人来人往的繁忙景象,穿着时髦衣裳的社会名媛,达官太太给她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别是大使馆内布置得富丽堂皇,各种公务人员穿梭其间,有西装革履的先生,有戴船形帽的女秘书。他们的一举一动是那样有派,充满趾高气扬的自信。从穷乡辟壤来的母女俩看呆了,她用幼稚的声音对姥姥说:“我长大了一定要做‘戴船形帽’的女人”。童言无忌,不经意的一句话为她的一生埋下了伏笔。
晚上,大姨妈拉着姥姥的手说:“你生了一个女儿是你的福气,今后老了你要靠这个女儿”。又说:“你母女俩留下来吧,跟着我互相之间有个照应”。性格倔强的姥姥考虑了一夜之后,对大姨妈说:“我母女俩还是回去吧,我不愿意麻烦别人(寄人篱下)。”
真是命运两重天,自此一别,大姨妈去了法国定居,此生再无相见。但是给小明圆的一生产生了重大影响。她身上既有求新求变追求光明的性格,又有勤劳勇敢、敢于担当的一面。
母女俩回到老家古城镇,为了生计姥姥嫁给了一个做“小生意”的侯姓汉子。前后又生下了“三男一女”,母亲成为家中长女,从此再无好日子过。
继父是一个性情暴躁的人,生活的重担压得他喘不过气来,心情烦闷时,就喝点小酒,赌点小钱,在外面招惹一下女人。被姥姥发现后,他揪着她的头发打她,小明圆使劲抓住继父的手,又咬又踢,护着母亲,继父可劲地骂道:“小兔崽子,老子供你吃喝,还给老子造反!”规定她每天到城外山上打一捆柴火,不少于五十斤,否则,回到家扣饭。
一个小女孩个子只有1米多,体重大概比一捆柴火重不了多少,十里长山来回也有二三十里路,别说打柴,就是空手走一趟,也很紧张。母亲常常完不成任务,不敢回家,姥姥瞒着继父外出去找,悄悄领回来,揣给她两个红署吃,安排在柴房睡下。
过了十五岁,母亲出落成一位高挑的大姑娘。继父再也不容她,一天到晚指桑骂槐,姥姥只有将母亲许配给一个“白”姓人家十二岁的儿子当童养媳。
在这个期间,母亲实在受不了继父的虐待和家庭的贫困,多次悄悄跑回奶奶家求援,认祖归宗,奶奶只留她吃一顿饱饭,带上一些必须品,不留在家中住。
奶奶家是富农,重男轻女。对几个儿子的教育舍得花钱,大儿子病逝。培养二儿子程道友,三儿子程道昌外出求学。分别在南京、无锡读了初中、读高中。在求学期间二叔、三叔受到了共产党的影响,回到家乡传播革命的火种。
二叔程道友是地下党的区委书记,三叔程道昌开始当上了地下党的情报员,往返于敌占区与新四军根据地传递情报。
一个家庭出现了两位革命者,在那个白色恐怖的年代是非常危险的。
两位叔叔瞒着老母亲,怕她受惊吓,但是,纸总有包不住火的时候,由于判徒的出卖,二叔程道友被敌人逮捕,严刑拷打坚贞不屈,被敌人活活用乱棒打死,将头割下挂在古城墙上,威胁老百姓。
奶奶闻知,忙求于内部的人把儿子的头用布包装回家中(尸首不许装验),怀抱着儿子血淋淋的头,痛哭到天亮,第二天家人发现老太太抱着儿子的头与世长辞了!
三叔程道昌自从哥哥牺牲后,正式投入新四军的部队,他也是母亲革命的介绍人。解放后在南京军区离休,2014年去世,享年九十六岁,付军职。
母亲当了童养媳后,不甘心自己的命运如此沉沦。她利用割草、放牛,做小生意的机会与人攀谈,寻找时机。她最爱听坊间流传的抗日故事,有一个游击队员被日本鬼子逮住了,要活埋他,鬼子指着挖好的坑问他这是什么地方;游击队员说:“这是我的家”,说完自己跳了下去,土渐渐掩埋了他人的人体,他呼着的口号渐渐微弱……
国仇家恨给她力量。一九四四年初他听说“新四军”部队到了淮阴,这是穷人的队伍,而且还要招女兵呢。她兴奋得好多天都睡不着觉,准备逃走参加新四军。她假装回娘家几天,朝着新四军的驻地飞奔。
千辛万苦打听到了新四军部队,人家不收她。问她要介绍信,她哪知道什么介绍啊,没有读过一天书,也不认识任何人。
当时淮阴、古城这些地区是共产党,国民党拉锯的地方、判徒、特务很复杂,共产党的队伍当然很警惕。参军的人要地下党组织介绍,她非常失望,猛然间想起自己的三叔程道昌也在新四军部队,但不知在哪个部队,虽然是自己的亲叔叔,这么多年没有接触,他会帮自己的忙吗?
她害怕离家时间长了婆家人会发现,立即赶回家中。第二天,她委托一位要好的乡亲,帮助她打听三叔的情况并托他带话说;侄女想念三叔,看在死去父亲的份上,见上一面。等待是焦心的,当她几乎感到绝望的时候,传来消息,三叔在家中等着自己。她又撒谎说回娘家,跑到了三叔家里,扑通一声跪下:求三叔介绍自己去部队当女兵,否则,自己这一生将要毁掉。三叔用力扶起了她,说我想办法给你开一张介绍信,接下来的事情就靠自己了,你怎样跑出去?别给两家人添麻烦,言下之意,婆家知道了绝不会放你走,夜长梦多。
母亲通过几天的准备,决定挺而走险。夜晚穿过危险、恐怖的十里长山,为了不给娘家人找麻烦,决定从婆家逃走。
在一个风高月黑头的晚上,她假装早睡。旧社会庄户人家没有电灯,只有油灯,为了节约油钱,家家户户都睡得早。母亲当童养媳三年了。三年来,为了保护自己的清白身,她绞尽脑汁称自己有病,不惜毁掉自己的名声。
这一天,她等了多少年,成败再此一举。
说起十里长山,荒芜人烟,茅草丛生几乎与人高低。常有野狼出没,野兔乱窜,蛇悉梭游戈。平日里,人们到山那边不惜多走几十路,就是要走捷径也要结伴而行。这里还是“强人”出没的地方,时常传出土匪杀人绑票、野狼吃人的消息!
时不待我,勇敢的母亲凭着几年前上山打柴的印象,向山的纵深走去。天空星星稀少,脚下坑坑洼洼,越走越寂寞,越走越害怕。每走一步如临深渊,每走一步如闯鬼门关!仿佛黑夜里有一双眼睛盯着自己,有一双手在抓自己……难道这十八年的生命就要终结在这荒山野岭?退回去,实不甘心!那是终生的痛苦,灵魂的痛苦!
就在这万劫不复之时,她感到前方有一点点灯火在闪烁。她以为是幻觉,揉了揉眼睛,亮光再次闪了闪,她犹如在大海中看到了陸地,拼命挪动双脚,向前划动。希望有一根救命稻草在前方等着自己……
终于来到眼前,在黑夜中有一座破烂的草房,窗内摇曳着微弱的灯光,随着风的吹佛时明明暗。
她轻轻地敲了敲门,再敲,屋内的人沉默了片刻,惊讶地问道:“是谁:,母亲听出是一男子声,她顾不得这一切,说了一声,大哥求求您开门吧!我家里人病重,连夜赶路迷了路,求您送我下山,那男子听声音是一女子,似乎放心了些,吱呀一声开了门,母亲给她躹了一个九十度的躬,男子被她的举动感动,举着火把,找来棍棒,头前带路,走了两个多时辰,终于走到一个崖口,他说,姑娘从这儿下去就开始下山了,天也快亮了,送到这儿吧。母亲说:大哥,谢谢了,你是一个好人,好人有好报。母亲渐渐走远,偶一回头,仿佛那位大哥还在招手、遥望。这就是传说中的十里长山唯一守山人。母亲给我们讲起这段经历,很感慨,解放多年后她回老家打听过这人,要当面谢恩!哪知山河依旧,物是人非,早已无踪影,这是他生命中第三个贵人。
到了新四军驻地,母亲参了军,穿上灰色的军装,打着绑腿,威武又英俊!
事情还没有了结。一个月后听说她的婆家人到处找寻她,到娘家大吵大闹要人!姥姥也“以毒攻毒”反咬一口,要自己的女儿,婆家理屈,又不知母亲的确切去向,只好作罢。
母亲参军后被分配在警卫班给一位首长当警卫员。
她非常感谢共产党救了自己,在部队叫干啥就干啥,没有一句怨言。
她干过警卫员、勤务兵、保育员、卫生工作者、保卫干事、人事干事。
由于苦大仇深,又有着红色基因,四六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组织上和同志们对她的评价,是:阶级党悟高,政治水平棒!团结同志,能处理好关系。
她参军前一字不识,为了迎头赶上革命形势的的发展,她积极参加文化学习班,从简单的字母开始,一个字往往忘了几十遍。她少睡觉、开夜差,把头发浸在水中打湿,清醒自己的头脑,在累积了上百个“汉”字后,有一天拿着报纸竟然能够念通。她乘胜追击,在很短的时间内摘掉了“文盲”的帽子。
有一天,所在部队为了迎接上级检查,整装待发。母亲被安排在队伍稍前,一阵爆风雨掌声,走来一位风趣而和蔼的首长,他挨个与干部战士握手,当走到母亲面前时,问道:你参军多久了?入党了吗?母亲心里紧张,一个劲地点头。几秒钟后,首长走过去,其他同志说:你知道这是谁吗?母亲说,不知道。“这是大名鼎鼎的陈毅同志,新四军军长。”母亲听后,非常后悔,应该多握一下首长的手啊!讲起这段经历,她说这是有生以来见过的最大的官,最平易近人的官。他代表了共产党的形象,高山仰止,没齿难忘。
一九四六年底,蒋介石撕毁和平条约,各个根据地、解放区紧急调动起来,与蒋匪帮奉陪到底,战场上下来的伤员越来越多。母亲与一些女同志被派后方医院护理伤员。战时医院条件差,缺医少药,没有正规的病房。租老百姓的四合院,伤员多房子少,空气流通差,容易交叉感染,给护理工作增加了很大的工作量。她们不厌其烦地把伤员一个个轮流或扶、或背、或抬到院子里呼吸新鲜空气,晒太阳,增强体质,防止感染,一天往返好多趟。
伤员中素质也参差不齐,朝护理人员乱发脾气,骂娘的也有。
有一次,刚把伤员搬出屋,天空下起了下雨,护士们忙招呼伤员们回屋。其中一名伤员嫌屋子挤,不愿回去,经反复劝解无效,还骂母亲的态度不好,向上级反映,母亲忍住眼泪向他道歉,甚至为他一个人撑起了一把伞,母亲全身湿透。那伤员被感动说了一句“对不起”,母亲说没关系,我们都是阶级兄弟。
经过艰苦的后方医院工作,女同志们对做“人”的思想工作、护理工作更有经验了。
一九四六年部队转防江苏省与河南省交界的根据地。组织派几名女干部到战时孤儿院工作一段时间(老照片:母亲,战友与孤儿)。
孤儿院主要经办单位:中国红十字协会。其中有烈士遗孤,战争孤儿、流浪儿童。母亲想起自己的身世,特别同情这里的儿童。为她们洗澡、唱歌、拈虱子、讲故事、哄睡觉。他们大多数受了惊吓,性格内向。女干部们个个都是多面手,二十四小时轮流守护在他们身边。
临别时,她们挨个亲吻着这些可爱的小脸,留影纪念。
一九四九年四月淮海战役,百万雄师过大江。母亲随着二野战军大部队南下,来到重庆,经过几个月的修整,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部队大多数同志转业地方。
母亲被安排到重庆市毛纺厂当保卫科长。在任内转业地方。
一九五O年下半年,又被重庆市公安局水上分局安排在重庆市朝天门水上派出所任第一任所长。而且至今几十年唯一的女所长。
在她任所长的几年中,走遍了辖区内居民所在地,了解解放初期重庆码头的复杂情况。
重庆是战时陪都、袍哥,把头盛行,国民党的残渣余孽遗留,都会对共产党的新生政权造成威胁。
母亲回忆往事,部队培养了他,组织培养了她,让她学会对每件事物的观察力、洞察力。是什么人,听其言,观其行,八九不离十。
母亲还是一位调解高手,经她调解的百姓纠纷、婆媳事件。大到治安管理,小到鸡毛蒜皮。大到入情入理的讲解,小到细小入微的处理方法,人们心服口服。
如今,弟弟渝进也是江北区重要片区警察,也是一位调解高手,多次被区评为先进个人,上电视被报道。这多益于母亲的身传。
母亲教导我们女孩子,此生学一技之长,专业技术,技多不压身。让我们终身受益。
母亲一九五二年遇到了她生命中的“真命天子”就是我父亲郑天民,生下了我们姐弟四人,生命有有延续。
一九六七年天降不测,父亲遇国难,那时候我们姐弟四人,最大的十三岁,最小的五岁。为了保护我们,母亲带着我们东躲西藏,一次,一颗流弹从我母亲的脸边飞过,差点打中。还有一次害死我父亲的坏人到家里将我母亲带走,弟弟大哭“妈妈别走”,我要妈妈!他们把妈妈带到他们的私设的监狱用黑布蒙着眼睛审问:你的大儿子多大了?妈妈灵机一动,我没有儿子,只有女儿,坏人似乎放了一点心,短期内不会有人找他们寻仇。妈妈问,我丈夫呢?我要见见他,歹徒说,他还在(实际上父亲被抓入他们的匪巢,短短几个小时就被他们活活打死,用刀捅死,草草掩埋在野水沟)你走吧,妈妈刚起身一个匪婆朝母亲的身后猛踢一脚,妈妈大叫一声:哎哟!妈妈回来后给我们讲了她的遭遇,我们全家抱头痛哭!
自从爸爸赴国难,母亲将我们一手拉扯大,白天要努力工作,她还是一个部门的负责人,为了养活我们她精打细算,那个年代是没有理可讲的。父亲被害后,银行仅有的存款也被冻结达几年之久。莫名其妙,欺人太盛。
二十几年过去了,我们长大成人。从幼年、青年、安家立业。母亲付出了多少心血,只有她自己得知。耗尽了她全部精力,拼尽了全部心血。为了给父亲申冤,正名!她踏破了多少门槛。
去世前几日,她好像预感来日无多,对我们说:“有一天我不在人世,你们一定要继续为你爸爸申诉、正名,这是我唯一的心愿!”并常教导我们:相信组织,永远跟党走!
母亲离休前是重庆市江北区人大委员会专职委员,是江北区德高望重的老革命之一。她去世送葬那天,聚集了很多干部、群众、乐队吹着她平日最喜欢的乐曲《我的祖国》《沂蒙山小调》为她送葬。人们感叹她的身世,感动她的品格,多年的革命生涯无愧于人生。古城女杰一路走好!
我的父亲、母亲是党的忠诚儿女。在她们身处悲惨境遇几十年,无怨无悔,坚信党,跟党走。
高天原土,报答不尽父母的养育之恩。
为了给父亲正名,我们等了五十二年!
希望这一心愿早日实现!
让无限忠于党、忠于祖国的优秀儿女早日安息吧!
2020年8月1日
相关阅读
- 08-062020年周易行业人物专题报道——记中
- 08-05古城女杰传奇——记母亲程秀英
- 08-05中国艺术家海外媒体展播——李赞集
- 08-05五谷道场重整渠道布局,未来能否借机进
- 08-04第六届+CAN中国餐饮思想大会在长沙举
- 08-04第四届40人智能照明论坛7月31日深圳



















